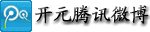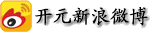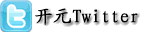日志
天上飞过的一只鸟
在中国学生会举办的舞会,见一个头发编成无数小辫的金发姑娘,就去邀跳舞,她脸上即刻漾起好看的笑,说不会.我说教她,就拉起她的手.她的确不会,我问:"会讲汉语吗?"她嗖嗖地吐出德语腔的"您好!谢谢!再见!"逗得我大笑,她也响铃似地笑,眼睛亮亮地看着我,她说她叫卡门.跳完舞我们交换了电话号码.一个星期后我们又见面了,在郊外一个幽雅的镇子那座木栅围住的小楼.我们好像是老朋友了,她热情地拥抱我,我不敢怠慢忙伸手抱她.她高兴地说附近正在举行Sommerfest(夏节).我们就一块去了,玩到下半夜才离去.我们沿著公路手拉手走着,间或有射著耀眼灯光的汽车从身边驶过.她说她常常独自出门旅行?也多次遭遇不测,但每次都"虎口脱险",当时吓得半死,后来还回味无穷.正说著她惊叫一声,看见一只正在爬行的癞蛤蟆.我说癞蛤蟆真丑,她说再丑也是一条生命,便蹲下身把"小丑"捧到路边的草地里.快到她家时她突然想起什么说带我去个地方,"嘎吱"推开一扇没上锁的木门,踏过荒草地来到一座破屋前,我心里毛骨悚然.她说小时候常和弟弟来这玩.她那两只蓝眼珠闪闪烁烁,我们搂在一起,我的眼还警惕地盯著暗处,什么都没发现,才少许放心地闭上眼.我们的双脚再也支撑不住我们的身体,才上了她家的楼,一块去洗澡,我发现她的皮肤到底比我们中国人白,毛发是金黄的,她说她喜欢我的黑色.那晚,一块中国"原件"置入德国制造的"机器"----运转良好.
我常去卡门的家.她说她从小喜爱表演艺术,只是由于父母的反对未能如愿,许多年过去了,艺术之心仍未泯灭,就去参加剧团的临时性演出,被认为很有天才,只是缺乏专业文凭没能大受重用.演出不常有, 也得去找点别的事做,打工对她是件恼火的事,坐办公室嫌其无聊,做别的又觉手脚不灵,好象她天生就是个超凡脱俗的艺术家.她性格很不德国化,有波兰血统,更多的是想入非非.我劝导,岁数也不小了,还是找个正当的职业好好过日子.她一听脸就变了色,说不用我管,即使她两个弟弟这么说,她也要翻脸.卡门曾经愤怒过悲伤过,轻身未果.我们常去她家附近的森林散步,遥望天边如火的晚霞,聆听从教堂传来的悠扬钟声,惊喜于小径上蹦蹦跳跳的松鼠.她说:"你们中国人看上去那么宁静,不象我们欧洲人那么容易激动暴躁."我回答:"那是儒家思想所致." "怎样才能学会呢?" "儒家思想渗透在中国的各个角落,你只要生活其中,就自然耳濡目染了."卡门的眼睁得老大.后来她真地就读起了儒家的书.
当时为了在德国的居留,陈教授建议我与卡门结婚,管它假的真的,把居留搞定再说.我试探地问卡门:"你这辈子想过结婚没有?"她猛然大笑,"我不敢想像两个人一辈子拴在一起会是什么情景."
我们还是分手了。尽管她说喜欢吃我做的中国菜,盛赞我是慕尼黑最好的中国厨师.她曾对她的女友讲,我是一颗中国性炸弹.
当我仰望天空那飞去的小鸟,就疑惑,那会不会是独往独来的卡门小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