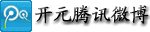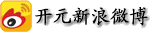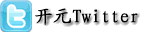日志
老百姓你算个"球"!
热度 1 |
 看了上边这行脏字,不要以为是"标题党"借机哗众取宠。在中国,一个位居"父母官"的县太爷,天天把这话叼在嘴上。但凡要与人民、百姓对话的时候,就把这个"球"字搬出来挥舞一番,骨子里对百姓的鄙视,让人怎么也看不过眼去。
看了上边这行脏字,不要以为是"标题党"借机哗众取宠。在中国,一个位居"父母官"的县太爷,天天把这话叼在嘴上。但凡要与人民、百姓对话的时候,就把这个"球"字搬出来挥舞一番,骨子里对百姓的鄙视,让人怎么也看不过眼去。时下,国内媒体的热点之一,就是发掘达官显贵们自己奢侈淫华、却置百姓衣食生死于不顾的暴料。虽然这样做在某种程度上貌似妨碍了"稳定"、"和谐"的大好局面,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自发的民意监督已经形似一把利剑,横扫了很多官方"自我监督"覆盖不到的侧面。
一名山西小县城的副县长浮出了水面。虽然人们并不清楚他是否也有贪污腐败之举,但他的"一夜成名"比贪官污吏更有甚之。这名高姓副县长其实也并非什么封疆大吏,本该听从党和政府的教导,即为人民公仆就踏踏实实地为人民百姓办实事,但每每当百姓找他公务,他便张口一个"球"、闭口一个"球"地乱骂,直到最后抖出了心里最真实的想法:你算老几?你算个"球"!这一下,全中国数亿老百姓不干了,把他扯了出来,一定要闹个明白:老百姓怎么就算个"球"呢?!
其实,这是一个有辱斯文的脏字,粗俗而下流。因为隐喻男人身上某个不安份的部位,所以几乎是肮脏、淫秽、卑微的代名词。至于被"公仆"搬出来称谓位居社会主人的人民百姓,实在不合时宜。
为了弄清"人民"、"百姓"与"球"之间是否有过必然联系,笔者查阅史料以求证。
"人民"是个复合词,但"人"与"民"先前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只有在今天这两个字才合起来用。在早期,"人"和"民"意义有别,大抵"人"比"民"高级。"民"最早出现于周代金文中,在甲骨文中并未见到,似乎是周人首创。"民"的字形很象拿一根芒刺来刺眼睛,故郭沫若氏认为是刺目之刑,或是黥面之刑;受刑之后的"人",成为了奴隶,便是所谓的"民","民"也就成了被征服者的代称。而后来,"民"原来的意义越来越淡化,"人"和"民"的界限也消失了。一个国家集团里,上至尊者、下至庶民,都是人民。
"百姓"又是怎么回事呢?几千年前,在黄河流域集中着几个势力较大的部落,有黄帝族、炎帝族、夷族和九黎族等。他们之间经过多年的征战和融合,最后形成了以黄帝、炎帝族的部落联盟,共同战胜了九黎族。其中黄、炎、夷三个部落的联盟,是由大约100个氏族构成的,因此统称"百姓",就是指那时候享有各种政治权利及社会权利的人民。
1949年9月,新中国成立前夕的政治协商会议,一国之主的毛泽东也一锤定音地宣布:"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从此,中国人民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主宰了自己的命运,实现了当家作主的权利。至少,在这个时候,人民、百姓还都是理想状态中的"主人",而并不是个"球"。
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官家开始愈发显贵、人民百姓则变成"球"了呢?笔者认为,从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起始,这种趋势便开始抬头了。经济上搞活了、富裕了,人性上也从政治压迫的框架下过渡到充分自由的状态,再加上社会缺乏对权利的监督和约束,很多官家手中的"公权利"得到迅速的膨胀和扩大,便在30多年的时间里一步步形成了中国"特色"---"公仆"们作威作福,而"拥有一切权利"的人民百姓却变成了"球"。
纵观眼下中国的社会矛盾,虽然表现形式各有不同,但究其根源,笔者认为都可以简化归一,那就是以高副县长为代表的官僚作风---当平民百姓为草芥,视民生冷暖为无睹,置民情民意以不顾,忽民怨民愤于不计。
虽然中国很多草根生命对"球"县官不满,但这位官人至少还有值得肯定的地方,那就是他坦率的秉性。很多高官显贵只是从思想上鄙视百姓,也把老百姓当个"球"、但嘴上从来不说出,而张副县长比他们都更有种,丝毫不隐讳自己的观点:老百姓你就算个"球"。
大概上小学的时候,语文课本里就有"人民诗人"臧克家先生的名句。"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把他摔垮。给人民做牛马的,人民永远记住他"。据此套用高副县长的口气回敬他一下,那就应该这么说:高副县长,你把人民当个"球",估计你离滚球、摔球、垮球也不远喽!
真想用我诗歌朗诵般的醇厚长音来颂赞他:高副县长呦,I服了YOU!
范 轩
2010年1月26日,于汉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