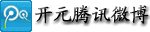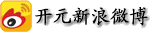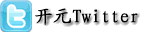日志
白夜的前言
热度 3 |
白夜的前言
日子好了,外遇多了,抑或日子根本也没好多少?——从精神的角度讲我毫不怀疑这点。
“浪漫”演绎到最后,纷纷地剑拔弩张,甚至趋向你死我活……
不能指望像《廊桥》里的牛仔那样从此收心再提不起寻花问柳的兴趣,像那位有着意大利血统的激情村妇在后来的日子里默默守着瘫痪的丈夫,然后天各一方的(偷)情人彼此思念致死,她身后的儿女们还能为其感动将两个人的骨灰合葬在那遗梦的桥下……
现在没有这样的传说了,编都编不出来。
尽管自廊桥的故事风靡中国后我们出现了一个好听点的词:婚外情,使人心看上去显得宽容,可实质的内容却似乎根本没变。
鄙视的还在鄙视,自卑的仍是自卑,盛装,难以掩盖心理的畸形。女人既委身了谁总是要夺回点什么的,且越多越好,不然岂不枉了那恶名。
当事者都还没理顺自己,更何况那些旁观者。
所以“情妇”们几乎人手一剑,双刃的,挥向对方的同时亦戳伤自己。这次回家发现我的发小不幸也身在其列。
形容枯槁,焦头烂额。
我说你这又何必呢,既是在玩火,干嘛不用这火温暖自己照亮别人呢,我不信玩火者必自焚。
是的,我相信温暖,相信温暖是人心的必须,不管它来自何处。
我也相信不管一种什么关系,只要它能够让彼此的灵魂释放、慰藉、抑或仅仅是歇息,那么无论是激情的燃烧还是温馨的守护,形式都不再显得重要,只要相互的心里真的能感到骇俗后的美丽。
要信任自己的感觉,我对她说。
其实,我又何曾信任过自己的真感觉呢,那一度激赏的水银泻地般的流淌,却原来最不宜在人的真性里奔放。
我只有在可以散布“奇谈怪论”的机会里,以凭吊的心,对美丽的死亡做调侃式的祭奠。
她可怜地瞪着我,我知道,那曾经有的、不能不算美好的感觉,早被后来的许多摧残了。
社会是这样的无情,令我简直钦佩那些不死的心——飞蛾,扑火。
好自为之吧,人们,在此我真的愿上帝与你们同在。
下面的这篇小文当年被发表在更名后第一次以新面孔出现的新报上,这让我有一种释然,觉得自己至少不像私下里以为得那么“离经叛道”。
时隔两年,我为此写了以上的话,看来看去的不知自己要说什么,这世界毕竟是太纷呈了,肯定与否时时都在转移着视线,我只愿目力所及的地方,能给我仍在祈愿美丽的心,哪怕是丝丝缕缕的欣慰……
白天也能懂夜的黑
他们都有名有姓的,但我在这里称他们为:大款,小狐狸和川妹子。
大款第一次带小狐狸来店里时,她挎着他的胳膊作小鸟依人状,可镜片后的目光让人不爽,好象在琢磨:你是怎么到德国来的?我心说你呢?看你也不象学生,没准就是赶上六四,在中餐馆里堂而皇之地涮起了盘子,现在涮成老板娘,看人就是这眼神了。当下并未计较,还一团和气地请教她的芳名,她说的是英文名,用的是港台味儿,籍贯却是中国偷渡风最盛的那个省,见我夸她的衣裳(没话了),便显出一副无奈的样子,“唉,没办法,就是喜欢买衣服……”然后“无奈”地倚着大款,继续看我,就是那神情让我想起了狐狸。事后证明我这个联想把她估高了,她没有狐狸聪明,如是,也不会让自己的结局那么惨了。
先显出惨样儿的是大款,半年里,眼见得头发就白了许多,眼睛也不放光了,(您知道,最初见面时,他那俩眼差点儿把我电着)每问及他的“狐狸”他就摇头摆手的说那女人正如何把他闹得寝食不安。
据说小狐狸整天都在迫他离婚,而他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并且也是事先交代好了的。为了这种协议,大款给她在家乡买了房子,这里买了餐馆让她经营,赚了是她的,赔了自然有他这个大后方补窟窿。这样的人一旦被带回家乡,你想想周围的人都会说什么,那小女子听多了当然就想把大款速速地归为己有。无耐攻势凌厉势得其反。大款焦头烂额之际居然还有精力安排我们到他的餐馆进餐,也许他想借此向我们证实什么。不知情的“老板娘”一晚上都很张扬。饭后驱车回“府”,在门前她反复强调那住所的临时性,说他的宅邸是如何之好,仿佛那即将也就是她的家了,然后很炫耀地对大款呼来喝去,大款乐的让她表现,象只憨熊似的给支使得气喘嘘嘘的,只是不时瞅一下我们,用那眼神说:瞧,我没说错吧,她就是这么无理的一个人。
他们分手后,小狐狸整日沉湎赌场,后来进了神经病院,再提起她来,大款只是说:“我其实把她安排的挺好的……”然后摇摇头,不想多说的样子。这种收场后的“薄情”曾使我对他十分轻视。
不知死活的大款再接再厉,他被中国女人迷住了,后来又在工作中遇到一位有夫之妇,非常欣赏,倾力接近,可人家根本不理他,他长时间的诉说这种遗憾和自以为是的可能,我心说你想什么呢。
大款还为此参加过国内的旅行团,企望遭遇激情,语言不通的障碍根本不予考虑,虽然给头疼的人猛发阿斯匹林泡腾,一路深受称赞,可惜没人了解他的意图,全程下来并无收获。继而在网络上又搜索了一段时间,时而兴奋时而沮丧地任情绪波动,屡北屡战,契而不舍。
后面发生的事收敛起我对大款的不逊,它还勾起了我遥远的回忆:我曾经工作过的羊毛衫厂,厂里那许多花儿一样的打工妹,清澈的眼睛因身体劳累和经济的窘迫而蒙上的淡淡阴翳,每天有那么些迎来送往的客商,有钱人,可有谁注意过她们,为这些淹没在粉尘和噪音间的美丽而痛惜过呢?没有,只有我这个还指望童话的人在累傻了的时候才会为她们做一做与水晶鞋有关的梦,是为她们不是我,因为我觉的她们远比我聪明漂亮勤苦且更没机会,就因为命运把她们降生在乡下,就因为她们有了弟弟,读书就与她们无缘了。既然世界上有那么个叫作“命运”的东西,那没辙的时候思寻思寻也实在是情有可原的事。
谁曾想这个圆梦的人就是现如今的大款,他注意上了她,在他合资的工厂里,理由近似于我的怜惜:象她那样的女人不该在那样污浊的车间里整日做那样单调的工作。对,是女人不是女孩,她离了婚还带着个九岁的儿子(顺便补充一点,以前的小狐狸也是离异带孩子的)以下的一切就顺理成章了,用大款的话说他给了她很多机会,现在她已经回去了四川老家,准备在大款的资助下干一项自己掌门的事业。
大款频繁地往返于中德之间,圣诞节是一定要赶回来带他的老婆去西班牙的某个岛上“补偿损失”的,虚伪吗?可对他的川妹子到不,他坦言自己是一个离不了婚的人,希望她不要指望,他会尽可能的对她好,下面的话才让我刮目相看“我不在的时候你不要总想着我,你也有你的生活,什么时候你遇上了合适的人,你尽可以去开始你的新生活”。不是我崇洋,国内的大款能跟他们的“二奶”如此表示吗?而且,我也没听说过有“拖油瓶”的“二奶”。
其实我不想用这个“二奶”词,尽管这看上去很象。
现如今世道的变化之快,每天都有那么多东西在进行着重组和再分配,道德和情感也难逃困厄,人很累,很累的人渴望着超脱一下累周围的沉闷,那么一些新的栖息地的形成岂不就显得很自然和说的过去了吗?
地震时大款心急如焚,让川妹子带上她娘和儿子先到北京去,并请当时也在京城的我帮她们安排下宾馆,川妹子婉拒,说除了住帐篷以外一切都还好,仅此就可见与前一位的不同。我见过她的相片,大款藏在他办公室抽屉的最里边,小心翼翼地捧给我后又谨谨慎慎地收回去,恐怕看坏了似的。
昨天他到店里来,说周末又要回中国了,这次办完公事,打算和川妹子一起进绵阳去,看看自己能为灾区再实际地做些什么。
大款走时,街上两座教堂的钟声正叮噹地响作一片,飘向漫漫的黄昏,太阳隐没的地方七彩云霞随风而酝将无数种色调混成瑰丽的景致,他那辆令人瞩目的车就在这短暂的辉煌下冲向远方的天际。
天快黑了。
钟声悠长,我听不出它和正午的区别。而正午的阳光通常被人们用来形容道德的力量。
现在这力量消遁了吗?不,道德的力量是永恒的,明天它还会出现,而明天也还有晨昏,有晚霞,有夜和夜幕上的星光,没有谁可以抵消谁,它们的转换根本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